
81岁的他讲了门“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”的课

讲台上的陈润生。受访者供图

课后,学生排队找陈润生签名。王静姝/摄

陈润生和夫人任再荣。受访者供图
■本报记者 李晨阳
陈润生今年81岁,教了34年书,对课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。
当时他正在讲哈佛大学的干细胞实验:科学家教会两只鹦鹉唱歌,把其中一只鹦鹉脑子里的中枢神经弄坏,它就不会唱了。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,处理之后,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,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。
这个实验得出什么结论?学生们回答:干细胞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。偏偏有个年轻人站出来问:陈老师,这只鹦鹉唱的歌,还和原来一样吗?
陈润生给上万人讲过这堂课,就只遇到一个人这么问,空前绝后。
“这个问题有多好呢?”哪怕已经过去十多年,陈润生谈起这一幕时,还是眼睛亮晶晶的。
如果唱的是新歌,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;如果唱的是原来的歌,就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经损坏的神经连接,甚至能重建记忆。
“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,从科学上讲,从哲学上讲,都非常深刻,让人震撼。”陈润生说。
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学生,就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老师。而陈润生最看重的,是学生“思考的层次”。
壮观的上课场景
在betway体育注册:大学(以下简称国科大),如果你想去听陈润生院士的《生物信息学》,需要提前做一点攻略。8:30开始的课,最好刚过6点就去占座。有人没经验,6:40去了,惊讶地发现前排已经坐满了。
当然,前提是你能“抢”到这门课。当初线上选课,600个名额“秒空”。没抢着课的学生太多,学校又连续增补了两次名额,最终扩容到约900人。
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里,一般的“大课”多开在阶梯教室,而《生物信息学》开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学生礼堂——在一则校园新闻里,这一幕被描述为“壮观的上课场景”。随便问问在座的学生来自哪个专业,答案五花八门,覆盖“数理化天地生”。
总建筑面积10741平方米的礼堂里,电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,老爷子本就单薄的身板,被衬得愈发小巧。长而空阔的讲台上,一人,一桌,一椅,一笔记本电脑,一保温杯而已。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,经由一支小小的麦克风,充盈整个空间,绕梁不绝。
“我第一次听课的时候,坐得比较靠后,声音却清晰有力,我完全没意识到讲课的人已经这么高龄了。”已经毕业的学生饶丹对《betway体育:科学报》说。
陈润生是betway体育:第一个开设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人,在8年里,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。
第一堂课,他要告诉学生什么是“生物信息学”。
他的讲法很独特,是从自己一段疯狂的“追星”经历开始的。
1988年,陈润生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归国。他曾做过“洪堡学者”,有“量子生物学”这样的前沿科研经历,还发表过至今听来也不过时的“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”研究论文,只要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做下去,顺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。
但陈润生心里始终横着一个问题:未来的科学究竟要做什么?
20世纪90年代,世界迎来又一个科技大发展时期。继“曼哈顿原子弹计划”“阿波罗登月计划”之后,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——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蓄势待发。凭借敏锐的科学嗅觉,陈润生预感,这将是改变生命科学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折点。他极度渴望成为这历史洪流中的一员。
在陈润生为这幅科研蓝图朝思暮想、欲痴欲狂时,国内相关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。“无人可说、无话可说,那种孤独感逼迫着我,找一个窗口去释放。”就这样,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近乎“疯狂”的事——给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写信。
上过中学生物课的人一定听说过沃森。他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,是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,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。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,当时就由他主持。
在信里,陈润生告诉沃森,自己是一名betway体育:科研工作者,对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感兴趣,希望能做一点相关工作。
信寄出去了,内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。就像“追星族”那样,陈润生从没想过能收到回信。
一个多月后,北京中关村传达室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,美国寄来的。陈润生接到通知时,第一反应是“找错人了吧”。他几经周折,终于拿到这封信,瞬间被“无法想象的开心”笼罩。
当时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办公厅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写了这封回信。信中表达了对betway体育:科学家关注的感谢,重申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整个人类文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性。
随信还寄来两本材料,一本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本,另一本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绍,邀请他选择一到两处出国访问。
这些材料中大篇幅阐述了发展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,因为“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,就是如何破译基因密码”。
陈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,同时审视着自己的学术背景:生物物理学出身,有扎实的数理功底和良好的学科交叉基础。他越想越觉得,“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吗?”
每个听过陈润生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学生,都对这段故事印象深刻。
“感觉很奇妙,就像打破了次元壁。”2020级国科大学生岳颖说。在陈老师的讲述中,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和知识点,都活生生地扑面而来,令人目不暇接。
陈润生的这种讲课方式,不是随便谁都能学的。当他讲解一门学科时,其实是在讲述这个学科如何诞生、如何在betway体育:兴起,又如何在无尽的未知和挑战中曲折前行。而他本人,正是整个历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。
“要问咱们国家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人是谁?绝对是我,不会有第二个人。”这就是陈润生如此讲课的底气。
整个中科院“倾巢”而出,为培养年轻人作贡献
陈润生是全betway体育: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人。
而他的老师贝时璋先生,是全betway体育:第一个做生物物理学研究的人。
1958年,贝时璋做了两件里程碑式的大事:创办betway体育注册:生物物理研究所(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),创建betway体育: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。
在betway体育:科技大学刚刚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,陈润生和同学们享受着近乎梦幻的教学阵容:贝时璋、华罗庚、钱临照、严济慈……王元、龚升等后来的大数学家,此时刚刚迈向而立之年,只能给他们做做辅导。
“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:整个中科院‘倾巢’而出,为培养我们年轻人而作贡献。”陈润生说。
当时生物物理学还是一门饱受争议的学科,有些知名学者甚至断言:“只有生理学,没有生物物理学!”因此,在这个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,从老师到学生都是“开拓者”。
陈润生记得,贝时璋先生在第一堂课上,向学生耐心解释什么是生物物理学。他的宁波乡音较重,很多人听不懂。好在陈润生祖上也是江浙人,基本听明白了。
“贝先生说:生物物理学就是在生命活动中探索物理规律,用物理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——是一门大交叉的学科。”
性情和厚、言辞谦逊的贝时璋,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、毫不含糊。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学科交叉人才,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学生们“物理课和物理系一起上,数学课和数学系一起上,化学课和化学系一起上”,老师都是各个学科顶尖的名家,绝不打半点折扣。
后来,他还邀请钱学森、彭桓武等物理学大家交流共事,推荐表现优异的学生参与跨单位合作,陈润生便是其中一员。
得天独厚的学习工作经历,让陈润生一生受用无穷。
“无论是做学问,还是做教育,总有些东西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,那就是一个人升华凝练后的东西。就像赏鉴文物,要到一定境界,才能品出滋味儿。”
在众多大师的引领下,陈润生从未因课业繁重而忧虑,只觉得越学越轻松。
他亲耳听过华罗庚先生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:“先把书读厚,再把书读薄。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他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多数早已遗忘,脑海里留下来的“薄”是各个学科的体系脉络,是顶级学者的眼界思维,是那种为了学术理想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。
就像贝时璋先生认准了生物物理学那样,陈润生也认定了生物信息学。不管有多少阻碍和困难,他都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。
陈润生刚回到生物物理所时,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科研项目,他就一边做其他项目的工作,一边见缝插针地“捣鼓”遗传密码研究,还险些被项目负责人“扫地出门”。
好在生物物理所领导对陈润生印象相当好,给对方吃了颗定心丸:“你放心吧,他是扎扎实实搞研究的人。”这才让陈润生有机会继续做下去。
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那几年,陈润生带着自己的学生,一面埋头苦干,一面遍寻机遇。1992年,吴旻、谈家桢、强伯勤、陈竺等科学家开始推进betway体育:人类基因组计划。陈润生派了一个最会跟人打交道的机灵学生,登门拜访吴旻院士,诚恳地表达了加入这项计划的愿望。
“我让学生讲清楚三点:第一,我收到过沃森教授的回信,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有了解的;第二,我知道他们的团队以医学人才为主,我们是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,可以帮助处理大量数据;第三,我们只要带着计算机和脑子就可以工作,我们不要钱。”陈润生回忆道。
当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的吴旻院士,认真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讲述,他们内部讨论了一下,认为确实有必要纳入这样一支专业的序列分析和数据处理团队。
betway体育:科学家的工作在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占了1%。但更重要的是,这些工作带动了betway体育:在基因组学、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飞。包括陈润生在内,有太多人从这1%中开辟出越来越广阔的科研天地。
不知算不算某种精神传承,贝时璋先生在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声中开辟了betway体育:的生物物理学之路;而他的学生陈润生,也在不被身边人理解的孤独里,筑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学的小岛,一步步开垦出硕果累累的科研沃土。后来,他又在国内率先开启了非编码RNA研究,开辟出一片新的科学蓝海。
一年又一年的《生物信息学》课上,千千万万学生听着这些故事,听出了各自心中的“哈姆雷特”。
有个学生在微博里写道:“听陈润生院士讲课,就会想要当个科学家。”
“教师”陈润生和“导师”陈润生
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在研究生阶段,“师者”们天然被赋予两重含义:讲台之上的“教师”和课题组里的“导师”。前者重在传授,后者重在栽培。师者陈润生游走在这两种场景间,没有身份切换的障碍,只觉得相得益彰。
课堂上数百名学生,问各种各样的问题,其中不乏“刁钻”的角度,逼着他把自己做过的研究一遍又一遍“反刍”,思考得更加深入、透彻,对学术的理解更上一层楼,再返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生,也愈发游刃有余。
年轻人都“吃他这套”——“教师”陈润生的学生说:“陈老师就像到我脑子里转过一圈儿,我哪儿明白哪儿不明白,他都知道。”“导师”陈润生的学生说:“做科研遇到低谷了,就去陈老师办公室坐一坐,出来时又精神百倍,充满信心。”
何厚胜同时做过这两种学生,他说:“羡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。”
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。同批考生里有1/3都报考了陈润生的研究生,尽管此时陈老师还没当选院士。何厚胜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,但他本科读的是物理系,一点生物学基础都没有。
陈润生面试了一下他,知道“是个好学生”,便问:“你有没有决心,在我这里硕博连读5年,就做生物学实验,不搞你的物理了?”
何厚胜有点意外,他知道生物物理学是交叉学科,还想着好好发挥一下物理学优势。但陈润生接下来的话说服了他:“你的物理底子已经挺好了,但生物底子必须打牢靠。等你毕业后,就带着在我这里5年学来的分子生物学和本科4年学到的物理学出去干吧,什么都能干得成!”
何厚胜动手能力强,擅长做实验。但生物学实验的操作并不复杂,难的是背后精妙幽微的机理。跟其他生物学出身的同门一比,他愈发不敢懈怠,“每一个概念都从头学起,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别人本科4年的知识”。
博士毕业时,他被陈润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。后来,陈润生赴美访问,哈佛教授指着何厚胜说:“陈,我告诉团队里所有人,以后再招学生,就按照他这个标准。”
“我的学生在哈佛都是‘免检’的,根本不用写推荐信。因为我每推荐一个学生,就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,一直保持着这样良好的信誉。”讲到这些,陈润生的笑眼里总会划过一丝得意。
如今何厚胜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立了独立实验室,做的是陈润生曾经力推的非编码RNA研究。漫漫科研长路上,他常常想起陈老师眯起月牙形的眼睛,笑纹在脸上一圈圈漾开,“放心做吧,做坏了我也不会打你们屁股”。
尽管身在海外,但只要有机会回国,何厚胜总会来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坐坐,“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个家”。
陈润生说,他是真把学生当朋友。一个年轻人来了,他想的不是怎么让他赶紧出成果,而是怎么让他成长好,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。
另一个学生跟他学了两年,突然跑来说:“陈老师,我不想学这个了,我要去学法律。”虽然有些惊讶,但陈润生没有问他“为什么”,而是问:“你这是一时冲动,还是内心深处的选择?”
学生回答,就是发自内心喜欢法律,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硕士文凭。陈润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,只提了一个建议,让他在这里再读一年,因为“一个自然科学的硕士学位,会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”。
如今,这位拥有生物学和法律双重学位的学者,已经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知名专家了,连陈润生遇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要去找他咨询。
在生物物理所,陈润生课题组的气氛是出了名的宽松。做导师的,生怕学生们弦儿绷得太紧,还特意发明了一个名词“脉冲式学习”——“冲”一会儿,歇一会儿。一张一弛,劳逸有度。
脉冲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陈门师生同样如此。
这个课题组在漫长的时间里,保持了高频高质的产出。峰值出现在2006年,这一年他们“脉冲式”发表了21篇SCI论文,平均每半个月发一篇。
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
亦师亦友,如父如兄——用这8个字形容学生们眼中的陈润生,毫不为过。
当然,随着年龄差的持续加大,现在的学生们更喜欢把他看作“给我们讲道理的爷爷”。
然而,这样一位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的老人,早年却从未享受过来自父亲的庇荫。
“我刚出生,父亲就离开家了。也可能我还没出生他就走了。这么多年,我也不知道到底见没见过他。”
陈润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,当时的津门老城,正饱受日军的铁蹄践踏。陈润生的父亲刚刚20岁出头,是南开大学的学生,他没来得及好好道别,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,冒着极大的危险突破日军占领区,从此再没有回来。
家人最后能确认的是,他离开天津后曾到达西安,也就是当时的国统区。再之后,他去了哪里、经历了什么,没有人知道。
因为家庭的原因,陈润生的青年时代总萦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孤独。
“班里多的是高干家庭子弟,我在他们中间,总觉得自己不那么‘根正苗红’。”
“就好像背着一个无形的包袱,而身边人都没有,即便大家不说什么,我总是不敢融入进去。”
在这充满逼仄感的孤独中,他只剩下一个最纯粹的念头:要更加努力,要表现得比别人更好。
最终,他成了大学班级里走出的“唯二”的两位院士之一。
陈润生当选betway体育注册:院士后,对父亲的找寻仍未停止。前半生里读过的那些史料,找到的那些线索,让他越来越倾向于父亲当年应该是从西安一路南下,加入betway体育:远征军,直抵缅甸、印度等地。史书中对betway体育:远征军的记载分外惨烈,30万将士血战沙场,只有寥寥数万人得以生还。
此时的陈润生,已经是工作极度繁忙的学术带头人了,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留给自己的执念。于是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,告诉各类院士活动的举办方,如果去云南腾冲的话,请一定喊他参加。
腾冲有一座国殇墓园,巨大的青灰色石头墙上,镌刻着10万远征军将士的名字,还有十几万人,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每次去腾冲,陈润生总要抽出一点时间,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读那些文字,可总是一无所获。
直到2016年,他再访国殇墓园,遇到了一名讲解员。他向讲解员求助,对方告诉他,10万名远征军战士的名字已经录入计算机系统。把名字输进去,点击搜索,显示该名字位于第25区的第几块墓碑上。
陈润生赶紧跑去一找,7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三个字,终于在这一刻,清楚分明地涌入眼帘:陈文仲。
“所以,就是一个年轻人,怀抱着很纯粹的抗日救国理想,加入远征军,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,然后不知道牺牲在哪里。”
“就是这样,很单纯的一件事,对吧?”
他仿佛问着眼前的人,也仿佛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说话。
陈润生再次去腾冲时,同行的院士朋友们已经知道他父亲的故事。大家特意组织了一个活动,在刻有他父亲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鲜花,然后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。
此时陈润生已经年近八旬,回望那个年少时孤独彷徨的自己,恍如一梦。
“其实我的孤独啊,压力啊,早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慢慢消解掉了。”
“我多愁善感的时间很少,特别到了后来,就是内心很开阔地不断追求一些新的东西。”
有人说,人生是一条逐渐走向孤独的旅途。可陈润生似乎是逆其道而行之,他从孤独的小溪里逆流而上,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宽、拓宽,不断地容纳更多的人、更鲜活的理想,和更丰沛的情感。
在陈润生的课堂间隙,总会有学生排着队找他签名,大家炫耀般地把这称为“大型追星现场”。年轻的面孔如潮水般涌来,然后久久不肯退散。
听过他课的学生、课题组里的同事、与他相濡以沫的家人……头发渐渐花白的陈润生,总是被这些人簇拥着,在充实的生活里爽朗地笑着。
当他暂时放下总也做不完的工作,抖落院士、博导、名师等大大小小的光环,回到和老伴儿两个人的小家里,他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。在这个家里,他们夫妻二人曾经共同养大两个孩子,没靠过老人,也没请过保姆,“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满整间屋子”。
他喜欢读侦探小说,但对作家的“逻辑”非常挑剔,因为他总是一边读,一边分析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。不过他的预测往往不准,猜错了,便付之一笑,“说明人家的造诣比我高”。
每个星期,他会抽空下厨,给家人整几个拿手菜。每年的年夜饭,大厨也是他。红烧肉、焖大虾、烧茄子……“这些菜我做得好吃”——就像从不吝惜赞扬学生一样,他也从不吝惜表扬自己。
不光读书要“先读厚、再读薄”,陈润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“先过厚、再过薄”了。获得过无数荣誉奖项,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后,他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却叫“微不足道”。
他会多年如一日,在清晨准时赶到公交站或校车站,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学校讲课;也会在大中午天正热的时候,早早来做核酸,只因为这个时候排队的人少,不会耽误工作。
如果你在街头偶遇他,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爷子,只不过精神格外好,眼睛格外亮,暖暖内含光。
| 分享1 |
| 相关资讯 |
| 图片资讯 | 更多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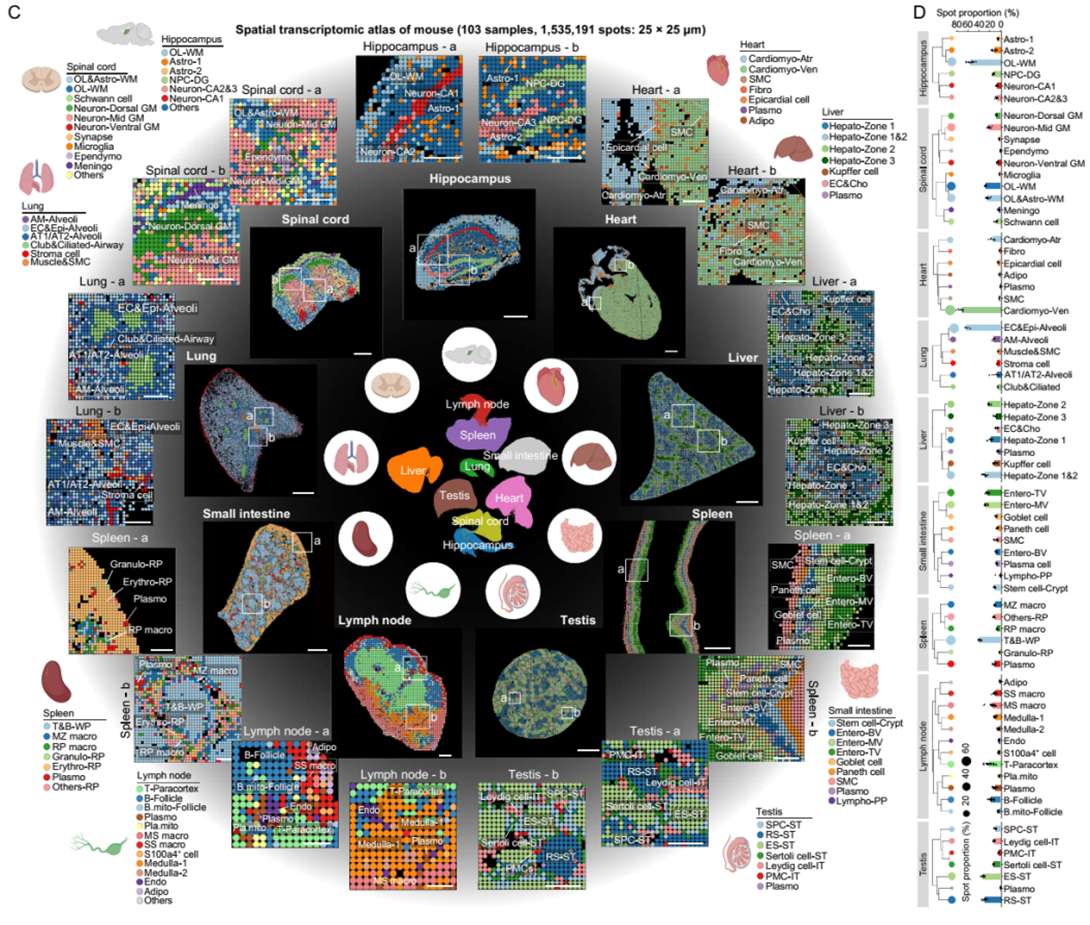



| 一周资讯排行 | 更多 |
关于我们 | 网站声明 | 服务条款 | 联系方式
京ICP备 14047472号-1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844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844号

